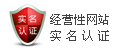日志
日志
裂变的开始·圆明园里的诗人与艺术家
三十年前,文学与艺术是整个中国舞台上最闪耀的明星,画画、写诗就像两个孪生兄弟,共同挥洒着、呼喊着时代的理想主义激情;
三十年后,“喜闻乐见”的娱乐明星登场,纯文学与艺术逐渐边缘化,唯有在拍场爆出的成交天价、由小说改编电影的过亿票房获得媒体聚焦的橄榄枝。
郭敬明概括得好,这是一个小时代。在小时代里,郭敬明的哲学是“歌者当歌,有人瞩目就别管大时代小时代”,也有艺术家如徐累,在他所称的“文化低谷”中一直做错题,直到时代发现了他。
文学与艺术,从同根生到各自为营的名利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人妥协了,有人仍在坚守……
诞生在80年代末,终结于90年代中期的圆明园画家村见证了时代的变色。
圆明园,是70年代末北岛和芒克等诗人举办诗歌朗诵会的地方,当它演化成盲流艺术家居住区的时候,这块土地,就更象征着延续着文艺基因的乌托邦。但废墟的沧桑感,又为乌托邦的命运染上了一抹灰色的基调。
80年代末,先后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高波、张念、康木等人,主动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成了京城较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
他们当中有人搞摄影,有人写剧本,有人学电影出身。但从文字和绘画的比例来看,画画的已经占绝对优势了。
到了1990年,曾经参与报道京城流浪艺术家的《中国美术报》原工作人员田彬、丁方等人,因其报社解体,也都纷纷撤退出来,同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福缘门村画画,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中心。
此后,越来越多的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圆明园画家村”由此得名,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象征。
方力钧就是在那挣了他的“第一桶金”,先是有汇率优势的老外去那买画,后是媒体围追堵截。当岳敏君等艺术家还在北大三角地的树林里做展览时,方力钧的作品已经放在了各大国际性美术馆展出。成名后的方力钧必须要把门锁上才能安心创作,而出门不敢走正门,要翻墙出去,最夸张的一次是,当他翻了一半,一回头才发现媒体正在后门外拍他的屁股。
批评家皮力将方力钧式的市场模式称为使馆输出通道,由于“在本土很难诞生个人的文化支持力量,各种事务所驻京办、在京的驻华使节们、好事的外国记者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和国际当代艺术的管道。”
1993年方力钧参加完威尼斯双年展后,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方力钧标志性的打哈欠的光头,并将中国人概括为泼皮无聊的一代。这个象征着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国门的第一次亮相,继而引发的一系列市场上走俏的连锁反应,便是由一个在北京逗留了5天的策展人博尼托·奥利瓦促成的。
“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考察使那些以‘揭露中国社会对于人性压抑’为己任的艺术家们在冷战刚刚消失的西方得了表彰。随之而来的大量经济收入使这些艺术家们享受了市场化中国的种种奢华,成为国内的新贵。”皮力说。
艺术家丰厚的报酬,也悄悄改变着诗人和艺术家的地位。
诗人佗佗是方力钧圆明园的邻居,同样搞创作,佗佗更早接触了新媒介。他在报纸上看到用电脑写作很美妙,第二天就揣上一笔钱到中关村买了一台386电脑,当晚兴奋地叼着烟围着这个新科技产物转了几十圈,认为电脑就像魔法石,打开就能催产小说。可没想到,开机后,噪音很大,轰轰乱响。
在《圆明园画家村札记》里,佗佗写道:我隔壁住着方力钧,那会儿他差不多要成气候了。我想,炸了我不要紧,要是把方力钧给炸没了,可就没法交代了。我愈想愈怕,最后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这位诗人半自嘲的内心独白,就像是时代更迭的最佳隐喻——诗人难以凭借诗歌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哪怕是中产阶级的地位,而艺术家则可以把作品变现,然后资本重组,开餐馆、藏古董,挤入名牌贴身的上流社会。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