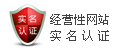日志
日志
批评的危机
21世纪以来,艺术学学科领域自身的空前拓展,媒介传播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都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艺术批评的学科生态。人们发现,不但“艺术批评”中的“共识”成为一个始终没有达成的目标,就连“艺术批评是什么”这个原本并不存在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本来,艺术批评以“艺术”作为本体并无可厚非。艺术的自觉和艺术创造实践的不断积累,是艺术批评开展的必要前提。人们从理性上对于艺术作品进行欣赏、描述、判断、评价,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发、点评、印象式的艺术批评,也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批评成果,从孙过庭到李长之,莫不如是,并且这种批评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很大的市场。然而,“批评”的第一次危机也正因此而产生。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印象式批评,除了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塑造出了一种批评家“居高临下”的权力身份之外,并不能够充分体现出艺术批评的理论难度和专业价值,缺乏学理化的表述形态,似乎“人人可为”,更遑论令人信服地去指导实践。
随着艺术批评学科化的发展,批评实践必然也需要一个“理论”化的过程,即通过学理化的语言、并且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将对于作品的印象通过一定的理论模式和方法加以归纳和总结,并且以理性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才是自觉的艺术批评。而此时,语言哲学的发展为批评的实践恰好提供了资源,在文学批评领域,贴近形式语言本身、体现为高度操作化的“批评模式”的“新批评”应运而生,并且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艺术批评的范式转型。
“新批评”对于艺术批评的转型和学科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践成果也是令人尊重的。以至于在后来的学术史上,我们大可以把那种贴近艺术作品本身、以理性解读形式元素的批评方法归之于“新批评”的范畴,它们接续了形式主义美学的分析传统,并充实了它的理论基础和应用途径。
然而问题在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样一个充满变数与新知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或曰“文本”本身,还是从艺术创造的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艺术生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不得不呼吁一种艺术批评的转型。从艺术内部的“自律”角度来看,当代艺术从架上的“形式实验”逐渐转向了综合材料所塑造的“观念”和“社会批判”的历史性转向,即艺术家更关注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批判的使命;而从“他律”的外部角度来审视,当代艺术创作模式、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可能不得到敏感的艺术批评家们的关注。由此也孕育了批评的第二次危机。
从批评自身来说,“新批评”的一枝独秀也必然导致极端落熟,人们只能把“新批评”所奠定的理论阐释框架和模式应用于对于各种艺术作品的解释,这显然令有所雄心和抱负的研究者所不满。因此在学术史上,“新批评”随着“文化研究”、“社会批评”的兴起而逐渐让出学术主流最终土崩瓦解。“文化研究”的兴起,在短时间内聚集和吸引了大量关心或者并不关心艺术形式问题的从业者参与其中。人们形象地把艺术批评家的工作对象描述为“从莎士比亚转向麦当娜”,试图来描述和把握这种批评的转型。
回顾整个20世纪,艺术批评从上半叶受到文学批评中“新批评”学派的影响而集中于对于形式构成等作品本身问题的探讨,让渡到“后现代”时期受到文化研究等人文科学发展前沿的影响而形成的各种理论奇观,其中出现了一条相对清晰的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的发展线索。但是,批评的第三次危机也正在逐渐积累。
在“文化研究”为我们汇聚了大量新鲜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经验的同时,人们发现,这种理论对我们增加关于“艺术”本体的认识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在“新批评”式微之后,人们会质疑这种固守于“艺术”本体研究的做法,但须知“文化研究”等后起的范式并不能够贴近作品本身,因而并不需要严格的形式、语言、技法等艺术学训练就可以轻易从事,但人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的一个现实,就是艺术批评能够为其他学科做出贡献之处却恰恰正在于此。“文化研究”式的社会批评,并非没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这不应该以艺术批评放弃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科特点为代价。
正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逐渐表露出对于艺术批评“缺乏共识”的某种焦虑,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不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艺术批评是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原因。可是,此时重回“新批评”占主导的时代似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艺术批评必须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重回艺术本体的原点,并且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与解读方式,才能达到“寻求共识”的学术目标。
根据自然科学的观点,只有能够在实验状态下体现出“信度”的结论才能够被接受。此时,20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为艺术批评的范式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艺术批评中的借鉴,正在成为眼下正在形成的一种前沿和发展趋势。这种艺术批评自然科学化的趋势在海外兴起的时间虽然比较早,但是也并不算很长。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直到康定斯基这位构成理论的集大成者那里,都始终没有使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对他基于个体艺术感觉的一些判断转化成实证的信度指标,因而康定斯基一方面接续了荷加斯、克莱夫•贝尔等人开创的“美的分析”这一形式主义的传统并将之固化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学科,但另一方面他的构成理论也常常因为“武断”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与怀疑。我们当然知道康定斯基的理论是有来源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他本人或者其他理论家、批评家只能用“感觉”来描述这种来源的话,在当代学术中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较早把实验的方法引入艺术现象研究的做法来自于心理学家。自从冯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实验研究的方法成为心理学的主要方法,这种实验研究一方面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心理学的实验,其实也是对于现代临床医学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高度借鉴。在冯特之后的格式塔心理学那里,人们已经开始用经典的“似动实验”来解释一些简单的艺术现象,是为一种古典的“控制实验法”。此后,随着科学测量仪器的发展,各种声学、电学、光学、医学、化学甚至军事学、犯罪学仪器设备先后进入到艺术批评家的视野,“现代实验研究法”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数学中的概率论和统计学技术获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是个人计算机的兴起和SPSS(PASW)、SAS、R、AMOS等各种统计软件的普遍应用,为统计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基于统计学技术的“定量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数量不断增加,现在也波及到了艺术批评的一些领域中来。
自然科学研究对于艺术批评的介入,首先体现为一种科学、实验的精神。在这方面,“信度”与“效度”的测量,是检验科学实验的两个重要指标。“信度”意味着在同样状态下重复进行同一实验的结果的稳定性,而“效度”则是指实验设计是否能够有说服力地对研究假设进行证明或者证伪。对应地,在艺术批评中,我们可以把“效度”理解为所采纳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艺术作品的含义或者说明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而“信度”则体现为这种解说是否能够与艺术家、接受者形成“阐释的循环”,亦即达到“共识”或者“沟通”的可能性。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把艺术批评看作一种“独自叩门”式的个人化行为,甚至看作一种不需要具备学术规范的“随笔”,但是,倘若想把艺术批评建设成为一门高等教育的专业或者独立的人文学科,这种科学精神就必须在艺术批评的实践中有所落实。例如,当批评家说出“大多数人如何如何”这样的论断的时候,就一定需要有调查研究的数据相支持,而批评家要论证“艺术欣赏会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这一命题时,就应该设计实验,将匹配过的儿童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实验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所谓批评的“共识”不是不存在。倘若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只是完全主观的话,艺术的标准就会失却,艺术在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和传播,而艺术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形成、把握这种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标准与创造的动态统一。
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各种实验的方法在艺术批评领域中的应用。对于此类技术,日本和欧美的一些艺术批评家和其他领域中关注艺术现象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初步的应用,也往往是诞生于欧美,经由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学术圈的传播,才于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后传入大陆。目前在大陆,心理学、传播学、广告学等艺术学的边缘领域中,已经各有一些学者,尝试把眼动仪(Eye-tracking)、脑电仪(EEG)、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性磁共振(fMRI)等研究技术应用于对于艺术现象的解释方面,我们期待它们对艺术批评带来某种令人激动的发现。
当然,我们必须警惕走到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极端化倾向中,误以为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艺术领域中的一切问题。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已经向我们表明“科学”自身的局限性。正因此,对于艺术批评中科学主义取向研究方法的褒举,并不意味着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种理论趋向的研究方法的摈弃,它们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代替。毕竟,统计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而现代艺术教育和现代学术所吁求的,恰恰对许多统计无法触及的问题进行阐释。
无论如何,当代批评家不能不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着高度的敏感与察觉,但首先应该立足于“艺术”这一本体和人文学科的学术定位。只有从这一原点出发,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批评才能够具备“学科独立”的条件和基础。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
本来,艺术批评以“艺术”作为本体并无可厚非。艺术的自觉和艺术创造实践的不断积累,是艺术批评开展的必要前提。人们从理性上对于艺术作品进行欣赏、描述、判断、评价,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发、点评、印象式的艺术批评,也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批评成果,从孙过庭到李长之,莫不如是,并且这种批评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很大的市场。然而,“批评”的第一次危机也正因此而产生。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印象式批评,除了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塑造出了一种批评家“居高临下”的权力身份之外,并不能够充分体现出艺术批评的理论难度和专业价值,缺乏学理化的表述形态,似乎“人人可为”,更遑论令人信服地去指导实践。
随着艺术批评学科化的发展,批评实践必然也需要一个“理论”化的过程,即通过学理化的语言、并且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将对于作品的印象通过一定的理论模式和方法加以归纳和总结,并且以理性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才是自觉的艺术批评。而此时,语言哲学的发展为批评的实践恰好提供了资源,在文学批评领域,贴近形式语言本身、体现为高度操作化的“批评模式”的“新批评”应运而生,并且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艺术批评的范式转型。
“新批评”对于艺术批评的转型和学科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践成果也是令人尊重的。以至于在后来的学术史上,我们大可以把那种贴近艺术作品本身、以理性解读形式元素的批评方法归之于“新批评”的范畴,它们接续了形式主义美学的分析传统,并充实了它的理论基础和应用途径。
然而问题在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样一个充满变数与新知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或曰“文本”本身,还是从艺术创造的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艺术生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不得不呼吁一种艺术批评的转型。从艺术内部的“自律”角度来看,当代艺术从架上的“形式实验”逐渐转向了综合材料所塑造的“观念”和“社会批判”的历史性转向,即艺术家更关注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批判的使命;而从“他律”的外部角度来审视,当代艺术创作模式、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可能不得到敏感的艺术批评家们的关注。由此也孕育了批评的第二次危机。
从批评自身来说,“新批评”的一枝独秀也必然导致极端落熟,人们只能把“新批评”所奠定的理论阐释框架和模式应用于对于各种艺术作品的解释,这显然令有所雄心和抱负的研究者所不满。因此在学术史上,“新批评”随着“文化研究”、“社会批评”的兴起而逐渐让出学术主流最终土崩瓦解。“文化研究”的兴起,在短时间内聚集和吸引了大量关心或者并不关心艺术形式问题的从业者参与其中。人们形象地把艺术批评家的工作对象描述为“从莎士比亚转向麦当娜”,试图来描述和把握这种批评的转型。
回顾整个20世纪,艺术批评从上半叶受到文学批评中“新批评”学派的影响而集中于对于形式构成等作品本身问题的探讨,让渡到“后现代”时期受到文化研究等人文科学发展前沿的影响而形成的各种理论奇观,其中出现了一条相对清晰的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的发展线索。但是,批评的第三次危机也正在逐渐积累。
在“文化研究”为我们汇聚了大量新鲜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经验的同时,人们发现,这种理论对我们增加关于“艺术”本体的认识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在“新批评”式微之后,人们会质疑这种固守于“艺术”本体研究的做法,但须知“文化研究”等后起的范式并不能够贴近作品本身,因而并不需要严格的形式、语言、技法等艺术学训练就可以轻易从事,但人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的一个现实,就是艺术批评能够为其他学科做出贡献之处却恰恰正在于此。“文化研究”式的社会批评,并非没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这不应该以艺术批评放弃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科特点为代价。
正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逐渐表露出对于艺术批评“缺乏共识”的某种焦虑,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不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艺术批评是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原因。可是,此时重回“新批评”占主导的时代似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艺术批评必须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重回艺术本体的原点,并且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与解读方式,才能达到“寻求共识”的学术目标。
根据自然科学的观点,只有能够在实验状态下体现出“信度”的结论才能够被接受。此时,20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为艺术批评的范式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艺术批评中的借鉴,正在成为眼下正在形成的一种前沿和发展趋势。这种艺术批评自然科学化的趋势在海外兴起的时间虽然比较早,但是也并不算很长。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直到康定斯基这位构成理论的集大成者那里,都始终没有使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对他基于个体艺术感觉的一些判断转化成实证的信度指标,因而康定斯基一方面接续了荷加斯、克莱夫•贝尔等人开创的“美的分析”这一形式主义的传统并将之固化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学科,但另一方面他的构成理论也常常因为“武断”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与怀疑。我们当然知道康定斯基的理论是有来源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他本人或者其他理论家、批评家只能用“感觉”来描述这种来源的话,在当代学术中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较早把实验的方法引入艺术现象研究的做法来自于心理学家。自从冯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实验研究的方法成为心理学的主要方法,这种实验研究一方面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心理学的实验,其实也是对于现代临床医学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高度借鉴。在冯特之后的格式塔心理学那里,人们已经开始用经典的“似动实验”来解释一些简单的艺术现象,是为一种古典的“控制实验法”。此后,随着科学测量仪器的发展,各种声学、电学、光学、医学、化学甚至军事学、犯罪学仪器设备先后进入到艺术批评家的视野,“现代实验研究法”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数学中的概率论和统计学技术获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是个人计算机的兴起和SPSS(PASW)、SAS、R、AMOS等各种统计软件的普遍应用,为统计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基于统计学技术的“定量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数量不断增加,现在也波及到了艺术批评的一些领域中来。
自然科学研究对于艺术批评的介入,首先体现为一种科学、实验的精神。在这方面,“信度”与“效度”的测量,是检验科学实验的两个重要指标。“信度”意味着在同样状态下重复进行同一实验的结果的稳定性,而“效度”则是指实验设计是否能够有说服力地对研究假设进行证明或者证伪。对应地,在艺术批评中,我们可以把“效度”理解为所采纳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艺术作品的含义或者说明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而“信度”则体现为这种解说是否能够与艺术家、接受者形成“阐释的循环”,亦即达到“共识”或者“沟通”的可能性。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把艺术批评看作一种“独自叩门”式的个人化行为,甚至看作一种不需要具备学术规范的“随笔”,但是,倘若想把艺术批评建设成为一门高等教育的专业或者独立的人文学科,这种科学精神就必须在艺术批评的实践中有所落实。例如,当批评家说出“大多数人如何如何”这样的论断的时候,就一定需要有调查研究的数据相支持,而批评家要论证“艺术欣赏会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这一命题时,就应该设计实验,将匹配过的儿童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实验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所谓批评的“共识”不是不存在。倘若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只是完全主观的话,艺术的标准就会失却,艺术在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和传播,而艺术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形成、把握这种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标准与创造的动态统一。
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各种实验的方法在艺术批评领域中的应用。对于此类技术,日本和欧美的一些艺术批评家和其他领域中关注艺术现象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初步的应用,也往往是诞生于欧美,经由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学术圈的传播,才于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后传入大陆。目前在大陆,心理学、传播学、广告学等艺术学的边缘领域中,已经各有一些学者,尝试把眼动仪(Eye-tracking)、脑电仪(EEG)、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性磁共振(fMRI)等研究技术应用于对于艺术现象的解释方面,我们期待它们对艺术批评带来某种令人激动的发现。
当然,我们必须警惕走到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极端化倾向中,误以为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艺术领域中的一切问题。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已经向我们表明“科学”自身的局限性。正因此,对于艺术批评中科学主义取向研究方法的褒举,并不意味着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种理论趋向的研究方法的摈弃,它们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代替。毕竟,统计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而现代艺术教育和现代学术所吁求的,恰恰对许多统计无法触及的问题进行阐释。
无论如何,当代批评家不能不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着高度的敏感与察觉,但首先应该立足于“艺术”这一本体和人文学科的学术定位。只有从这一原点出发,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批评才能够具备“学科独立”的条件和基础。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
评论(0个评论)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