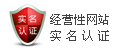日志
日志
徐渭——隔墙犹笑老梅花

五月莲花图 徐渭 上海博物馆藏
二月廿二,听闻李世南先生位于琉璃厂的艺术馆新展布好,名唤“人花无相”,便走去看。心想应是先生的花卉写意之作,走到,方见得乃是花卉与人物的打散,记载下先生壬辰年的种种悲、种种喜,与春俱来,与秋偕去。和往常一样,艺术馆内落红常寂寂、花叶自鲜鲜,多半时间是我与馆员张君两个人打转。上午十点半许,李先生与李师母步行而来,笑靥如春,我在门口活跳跳独自迎接这新画展的老主人,又惊奇又欢喜,还有这样清奇的寂寥与热烈的相聚。在明亮的春日底下。琉璃厂东街玉兰吐秀,招牌林立。新兴的画坛飞将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抖空竹的汉子在街头缄默。没有多少人认得素衣简约的先生就是艺术馆门口那笑如虚空的画家本人吧?
李先生在春日下灿灿生辉的笑,极具“无心之感”的“写”意味,隔墙犹笑。
杨儒宾教授尝撰宏文论“山水诗也是工夫论”,有妙悟曰:传统中国的经典“美学”实该称为“感学”。而15世纪的日人世阿弥在《花镜·上手的感知》中,也曾经借鉴中国《易经》以“咸”为“感”的灵感,提出“感”不仅高于“技艺”与“心”,并且超出了意识,是“纯然直觉的境地 ”“真正的感动,是超越心智的一瞬间的感觉”,并且这种“境地”是可以经由“工夫”路径获得的:
在名家的艺位上,具有“无心之感”,才能达到学满天下的高位。这需要不断刻苦钻研和反复修炼,方可以使“心”达到最高境界。
时隔千百年英雄所见之同者自然不止如上两位。西晋郭象所倡“无心应物”“心与物化”,无妨同样说的都是主体的转化。中国语境下的“感”“感物”“物感”,在先秦两汉时代首先是哲学范畴,尤其是生命之学范畴,所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演变为审美范畴”,未始不是经过美学至上洗礼的“五四”与后“五四”学者的自我作祖,尤其被“五四”追认为性灵鼻祖、物欲先河的“晚明想象”中,此意尤其显豁。这里不妨再以中国画苑大写意的创始人物徐渭为例。
徐渭生平多能,以戏剧名、以诗文小品名、以书法名、以绘画名,与其自我定位相左的是后世最青眼他并不十分在意的泼墨大写意绘画尤其花卉。徐渭的人格诚然有所偏颇,气性也很不圆善,清人松年《颐园论画》中已经概括得颇为全面,包括“孤冷拒人,自觉清高,刁钻古怪,耍名士脾气,乖僻,矫枉寡情,恃才傲物,心地偏狭,修怨害人”等等,几乎都是针对徐渭发言。但徐渭的绝望感是否只是停留在“一种幻想,一种因具体事物而引起的压抑”呢?在徐渭乃至明代中叶以降种种离经叛道的现象中,我们其实不难读出,由于面对更高的精神需要,例如宗教需要,伦理本身同样会陷入要求被超越的紧张和冲突当中。这类现象的确颇让我们想起斯瓦本神学家阿诺德(1666—1714)在《公正教会与异端历史》中的断言:从原始基督教到宗教改革,构成了基督教历史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上真正的基督教徒乃是那些被认为是异端的人。这类人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奇峰突起,自然不能绕过魏晋的名士,以颓废放诞上演严肃认真。明人徐渭与救命恩人张元忭之间无法避免的冲突恐怕也当算入此类冲突。后者敦于礼法,较易在伦理本身安顿性命,而徐渭高超的审美能力则使他获得了越过日常伦理向更高的精神力量跃迁的可能,对他而言,道德(伦理)尚不足以构成精神的最高层面,尽管徐渭可能到底没有完成这一跃迁的彻底。在克尔凯郭尔式的人生三境界中,审美人生通过契机可以飞跃到伦理阶段或宗教阶段,伦理人生通过选择也可以飞跃到宗教阶段。没有某个阶段是自足的,三个阶段中任一阶段的绝对化都会带来自我的窒息。徐渭身处的明代中叶的伦理社会,有可能遭遇了类似的僵局。
徐渭并不像他后世草率的模仿者一样追求所谓“绝对自我”,成为所谓“独一无二”。“不求形似求生韵”(《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对他更多意味的乃是“体虚故神,有物便实而不化”(王畿《水西精舍会语》)。诸相无常不失故我,诸相非相乃如来相,山河大地一花一叶,皆在常中性在相中。仅仅拘泥于“写形”(造型)而“体物”,诠以佛学名相,未免就是只能识得六识之内世界。业已转化的主体具备不落方所不涉时流的能力,如此观物就不会落入一般意义上“物”的层次。不落入“物”的层次,“人花无相”才有了可能。物我同根,俱在化中。
气化精微的生命状态其“适应社会”往往也是有限度的。否则一味平庸就可算做最崇高的德性了。徐渭的“桀骜”与“叛逆”只有基于一层更真实、精微的生命层面散发出来,才能获得意义。这种与世对立同样有“不容已”的成分,“和光同尘”作为德性同样有其限度。“天趣烂发”并非随意涂抹,而是需要主体首先具备“知天”的能量与能力。如果说徐渭的笔墨意境的确有强烈的“冲突”,那么是何原因使得冲突如此强烈呢?徐渭之“感”冲撞现实之墙引发的疼痛,如果只有怀才不遇、托足无门的简单的现实不满,他的笔墨不会引发后世如此旷日持久强烈的艺术共感。这种共感深藏了一个深远的历史共业、人伦共性:既然个体存在一直渴望从破碎剧痛之现实状态中获救。“把世界从邪灵的作弄之中解放出来的积极运动”与“破坏世界秩序、扰乱心灵和谐的消极力量”往往悖谬地成为一体的两面。
对青藤人品乃至画品贬抑至极进而更将“文人画”价值一扫无余的论者,当代或者可以徐建融先生为代表。徐先生针对晚明社会与道德流弊的痛心自有种种见地,对于“士人”价值重建的推举也有种种道理。只是“士人”与“文人”如何划分阵营,当不至仅见于显像的社会文化的具体承荷,这里同样有“内境工夫”可言。一味责备“写意”传统无非为“文人”业余戏墨而缺少造型的专业能力,未免粗陋,犹如徐先生亦不得不承认徐渭的笔墨艺术自有不可磨灭的风格魅力。则更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深究此艺术魅力之源缘何而起,此艺术魅力能否经由“工夫”获得?
生命的最后十年自觉选择避门不出拒食谷物,徐渭的精神状态当然并非“癔病”所能尽之。“渐修积劫”与“一超直入”未必不能不一不二(二者界限当然也不必一概抹杀)。古典与现代之间更非社会与个人、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简单对立——而是我们需要重新对于“个人”恢复其丰富丰沛的内涵。“毋我 ”“克己 ”“为公”诸概念固然高妙,更当有更为深切精细契合人性的诠解。对于“文人”趣味的贬抑紧张,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反思最有切身伤痛,“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日知录》)——此乃针对“士当以器识为先”(宋·刘挚之)而发。倘无器识在先,则士何足贵、何以存?
归来看月历,才记得廿二那天刚好是春分,天门始开。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评论(0个评论)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