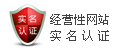日志
日志
封面人物访谈:苏新平
1)1992年,苏新平版画个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你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展览之一。展出的作品予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1986年创作的《牧童》;1988年的《飘动的白云系列》;1989年的《躺着的男人和远去的白马》以及1991年完成的《空旷的草地系列》等。与众多热衷于少数民族题材的艺术家相比,你对蒙古族牧民生活的表现颠覆了人们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自由奔放的生活的浪漫想象,近乎残酷地揭示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的单调和枯燥。这批作品不仅得到批评界的一致肯定,也同时获得了国际艺坛的高度关注。作为版画家,你无疑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毕竟古今中外,美术史上真正以版画扬名立万的艺术家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不仅如此,你和红门画廊的合作,也为你作品走向国际艺术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出乎意料的是,在一片赞扬声中,你却悄悄地转身拿起画笔,画起了油画。由版画转向油画,对于已经在版画领域获得成功的你来说,难道没想过一旦转型失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吗?
我的那批表现草原主题的版画作品的确赢得了不少的赞美声,同时也赢得了不少利益,但这些于我来说都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个时期的我很单纯,只是想着画画,并且画的非常努力和认真。当时,我对于题材并没有刻意的选择,我只是在尝试画面语言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有所表达,所以很自然地选择了自己最熟悉和最眷恋的草原。不过,那时的我的确对当时流行的表现少数民族方面的作品很不认同,觉得那些画很表面,很假,也很做作,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才使我持续地画了一批表现草原主题的作品。
其实,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讲,我的重点并不在于表现什么,而是在于寻找个人表现的语言方式、方法,画草原只是我的一个“借口”。因为我从小生长在草原,对草原比对城市更熟悉,所以只好选择草原题材,其实我是借用了草原的外观来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我学的专业是版画,而版画中石版的绘画性非常适合我的需要,所以我选择了石版的技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心理,当时也很想用油画的方式表达,但之前我并没有画过油画,更不知道油画的语言方法,那个时候老师是不允许学生跨专业的,所以石版方式成为我唯一可以利用的表现手段,当然,石版这种表现手段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运用的也得心应手,比如石版的硬度、版面的颗粒、铅笔接触版面的感觉和落笔后的效果等,现在看来这正是我的石版画作品的特点,也是我语言独特性所在。我想多数人肯定我作品的原因也在于此。至于题材的选择,与当时很多艺术家的“猎奇”表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个时期,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当作品有了一定的数量时,便“水到渠成”的在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但展出后赢得大家的好评是没有想到的,但远远没有达到“成功”的高度。提到市场,我的确很有运气,红门画廊只是原因之一,当时也有一些外国画廊同时接受了我的作品,这一点在国内画家中的确是屈指可数的例子,对于我来说也是意外之喜。
我从版画转向油画时,并没有觉得版画和油画有什么差异,我做版画时是把版画当绘画作品来对待,油画也是如此,它们只是技术上的不同罢了,心里其实没有什么障碍,选择何种手段都是自然而然的,自由表达是我那时的最大愿望。我当时没有想过画油画或转型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这种成败的概念我从来没考虑过,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因为我从没将成败当成负担,既然选择了做艺术家,就不会在意成、败利益之事。的确有不少人,甚至朋友对我当时的变化感到突然,但我至今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不迈出一步怎知问题所在?
2)为什么没有像一些版画家那样,用影像、装置、行为等当代媒介进行创作,而选择了油画这种在许多批评家看来已经被宣告死亡的艺术形式?
在我看来,影像、装置、行为等新媒介、新材料确实有着自身的特质和张力,这些是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但传统媒介和材料也有着自身的表现力和独特性,并且仍有继续挖掘的可能性因素。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媒体都存在着如何转换为个人语言的问题,如果能够转换为个人独特的语言方式、方法,那么他就是成功的,即使是传统媒介同样也有转换为观念性语言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上很多成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艺术家对自身、对世界、对媒介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又没有个人的语言方式、方法,只是套用理论概念或抄袭他人的样式,那么这样的作品不仅不是当代艺术作品,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艺术是不能以媒介来划分的。所谓的“油画或其它传统媒介、材料已经被宣布死亡”、“艺术已经死亡”等说法,多是出于某种需要或是某个特殊条件下的策略罢了,如果当真,艺术世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恐怕会苍白的可怕。
对于我个人来讲,选择油画只是选择了油画这种媒材,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绘画技巧和绘画趣味,因此我不是在画油画,而是用油画材料制作作品,其语言方式、方法都是具有很强的个人因素的。我之所以还没有完全选择新的媒介和材料还有一个关键所在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和自身对绘画的迷恋,此外,我始终抱着绘画有可能转换为适合自己的观念艺术语言的幻想,我个人十分清楚这是给自己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也许能够找到一条路成功的走出来,也许永远是个幻想,何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成败不是艺术家考虑的问题。
3)90年代初,你在创作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语”期,“失语”的原因何在?
90年代初是我走进艺术界和艺术生涯起步的时期,1992年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个展,1993年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展,这两个展览都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好评。从中国美术馆个展后,我就开始了香港、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巡展,重要博物馆、艺术机构和藏家开始了大量的收藏,商业活动紧随而至。按常规来讲,我本来是可以沿着已有的模式继续创作、展览、销售,并顺利的走下去,但是在美国的半年时间改变了我的认识和方向。在美国的半年中,我每天跑博物馆、画廊,见艺术家,耳闻目染逐渐让我对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现状产生了动摇。首先对传统艺术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传统的经典艺术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努力的目标,但当我在大都会博物馆和卢浮宫反复看到成千上万件曾经令我仰望的大师作品时,我由开始的兴奋,到渐渐的麻木,再到后来的疲倦,当最后从心里产生一种排斥的感觉时,我突然意识到,前人建立的艺术高度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只能产生于当时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也只代表那个时代的人文理想和艺术高度。今天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文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可能重复它们所走的道路,既无法企及,又没有必要,与此同时,我对比的看了苏河艺术区和现代博物馆丰富的当代艺术展览和活动。我发现当代艺术与今天的关系,或者说与我的内心和精神诉求很容易产生互动,而且越看越有感觉,并且能够从心理和思想上产生共鸣。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我又接二连三地往返于各个当代艺术展览和艺术家的交流中,随着对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制作的方法的了解,我对于观念艺术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改变,虽然仍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但这时的我已做出了选择。在回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了新的尝试,边想边做,大致持续了两年多,“欲望之海”系列作品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虽然这批作品仍然使用的是传统油画的媒材,但在思想观念上,我开始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开始重视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许这就是你讲的所谓的“失语期”,但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失语期”,而是“转型期”。
4)与你熟悉的版画相比,油画这种媒介在创作表达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个人将版画和油画都视为绘画范畴,它们的区别在于:版画是间接性绘画,而油画是直接性的流动绘画。从它们的区别中可以看出,长期从事间接性绘画的我有着一种直接表达的欲望,尤其是那个阶段我总期望可以随时随地都能拿起画笔去表达,而且希望想的和做的能够连贯起来,也许这就是让我迷恋油画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我想尝试吸收版画语言的一些特点来画油画,比如设计感、平面性和套色叠压等方法,我最近的作品开始使用油墨滚子来取代油画笔作画,其语言特点越来越远离绘画的模式,画面效果更加单纯和强烈。我认为油画材料存在的可能性因素很多,比如与立体的或其它媒介材料的结合等,也许这些都是油画等绘画媒材的优势所在,也是令我着迷的原因。
5)还记得第一次以油画家身份公开展示作品是在哪一年吗?大家对作品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油画第一次在国内露面是在90年代冷林策划的第一次国内当代艺术拍卖活动上,我送拍的是一件“欲望之海”系列作品,这件作品被一位法国收藏家收藏了,可能这是我的油画第一次在国内露面。
第一次油画个展是在英国伦敦的当代艺术画廊,紧接着我的一件大型作品“世纪之塔”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蜕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展”,展览结束后这件作品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由于这两个展览,这个时期“欲望之海”系列的30多件作品都被美术馆等机构和藏家所收藏。今天看来,作品迅速销售掉并不是一件好事,看似幸运的我,其后果是在之后的几年里没有作品参加国内的展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失误。虽然当时在国外关于我作品的评论和报道很多,但都没有让我直接听到更多的真切反馈的信息。
6)有评者这样写道,“风景使苏新平找到了自己全新的绘画语言,”“《风景七》则使苏新平拿到了世界艺术家的通行证,这幅具有当代性和世界通行魅力的画作被用在海报和画册封面上,一个没何手臂的小人穿行于荒塬——这更像是苏新平无数次散步中的一次,他脚下的北京或者说他笔下的北京令人手足无措。”我想了解的是,和你自己的作品相比,《风景系列》作品中“全新的绘画语言”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风景”系列作品是近些年的作品,“风景七”是其中的一幅,促使我画这个系列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过程对我个人生活及内心产生的冲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表达愿望;二是这种表达的冲动又让我产生了尝试不同绘画方法的欲望。90年代中期,我的画室从市中心的王府井搬到了20多公里外的乡村,每天往返于城乡之间,我目光所及是一望无边的绿色田园景色,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眼见城市边缘一座座楼房矗立起来,曾经的树木、农田在消失,我开始还在为城市的现代进程而自豪,但有一天我发现高楼已经包围了我曾经远离城区的画室时,自己才突然感到不知所措了,这时再看画室周边,再也见不到曾经的田园风光,有的只是林立的水泥建筑,它们如同没有生命的荒塬,荒芜又凄凉。我面对这些看似缓慢确是急剧变化的现实时,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那时那刻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促使我进入了复杂而深刻的反思,同时也促发了我用艺术方式表达的强烈诉求,接下来便是如何画的问题。我发现原有的绘画语言方式不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思想观念,尝试新的语言表达的课题由此而提了出来,由于其它媒介材料还不能准确把握,再次回到绘画本身寻找适合自己的语言方式、方法成为了我唯一的选择,又由于我长期以来对绘画直接性和流动性的兴趣,所以我就围绕这个线索展来了实验性的探讨。因此,可以说“风景”系列作品是对绘画性中的直接性和流动性向个人语言转化的实验性探讨的实现过程,具体的工作方法就是在不设定前提(不画草图)的状态下,凭借第一笔落于画面的感觉,从一个局部入手,每一笔不重复地向四面推进,直到铺满画布为止。由于这种方法摆脱了反复塑造的传统绘画模式,因而在绘画过程中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因素,整个绘画过程中必须全神贯注于脑、心、手的统一,所以这样的绘画语言方式、方法与我的思想观念是统一在了一起,其实这些正是我所追求和达到的目的。
这一系列的前期作品曾在今日美术馆展出,你提到的评论也多是来自这个展览,有关你提到的“全新的绘画语言”的评价是在一些杂志上出现的,我认为这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个人认识,还有不同的评论也出现在杂志等媒体上。我作为艺术家,做了想做的事,事后的评价无论好坏,自己都会以平常心态来对待的。如果说“全新的绘画语言”或者“已拿到了世界艺术家的通行证”等评价的话,肯定是有些简单化的,在我看来,艺术的价值不决定于此,艺术家的理想和目标也远不止于此。
7)“一幅具有当代性和世界通行魅力”的画作,在你看来,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特征?
8)尽管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倾向于影像、装置、行为等新的艺术形式进行多种试验和探索,但显然还有不少艺术家执着于版画、油画这样的传统形式,通过不断的调整,来解决一些当代问题。在你的艺术实践中,最令你困惑的问题是什么?
我并不认为选择了新的媒介手段的艺术家就是当代艺术家,他的作品就是当代艺术作品;而选择使用传统媒介材料的艺术家就不是当代艺术家,作品就不具备当代性,这样的判断未免有简单化之嫌,这也是国内艺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存在的误区。新媒介材料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摆脱了传统媒介所承载的传统审美的负担,并且材料本身确实具有单纯、直接和富有张力的特点;而传统媒介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其语言模式和特点确实限制了它的表现张力,加之所承载的负担,其语言突破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但是并不能说传统媒介失去了当代性语言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当代艺术家或当代艺术是不能用媒介来定位的。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取决于观念上的创新和实验性的探索,还取决于艺术家对今天的社会和文化的敏感性,并且有个人化语言的传达和对当代问题的独到表现,通过这样的传达和表现,艺术家能够提出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如果艺术家用新媒介表现的是别人的概念或用别人的语言方法表达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其作品不仅不具有当代性,甚至不能称其为艺术家;如果艺术家能够在传统媒介基础上实现个人语言的转换并且能够准确地表达个人对当代问题的思考,那么他的艺术一定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但在传统媒介的局限性中走出一条新路或有所突破其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正是由于它的难度和挑战性,才激发出了不少艺术家突破局限性的热情。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清楚传统媒介的局限性,但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个人语言表达方式、方法的道路。
目前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时间得不到保障,即缺少思考的连续性和持续的实践,从这一点来讲,承担过多的社会工作对个人艺术创作还是有所影响的。
9)你是艺术家,既搞版画又画油画;与此同时,你还是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的院长,版画系主任。你是各种关系的纠结者,又是众多矛盾的统一体:传统与当代,保守与前卫,规范与创新,教学与创作……从局外者来看,这其间矛盾重重,有些似乎很难调和。不知你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平衡这些关系和矛盾?
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虽然主要任务是学知识,但我也在幻想着实现个人的艺术理想之梦。其实在那个年龄段面对的问题也很多,剪不断理还乱,但是面对问题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学会了怎样梳理清楚各种矛盾和关系,人逐渐就由感性变得理性了。毕业后,我做了教师,同时也在做艺术,这时,我要面对如何在做好教师工作的同时做好自己的艺术,而且还要面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家庭的关系等问题,如果仅凭感觉走,理不清轻重缓急,我的生活肯定会“一团乱麻”,但一次偶然性的事情让我一下醒悟过来。当我第一次去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在美院当教师,他又问我去美国干什么,我说自己是艺术家去美国举办展览,他停了好一会,又看我的材料,然后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时我才明白身份应该明确才对。我由这件事受到启发,开始清理正在面对的混乱状态,一段时间后,逐渐理顺了所有的事情——工作就是工作,做艺术是个人的事,其它不与此缠绕,理顺头绪后,所有的纠结也就不存在了。再后来,我又承担了一些行政职务,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很快就会理顺轻重缓急,所以事情很快就不会相互干扰了。对我来说做艺术肯定是最重要的,所以思考和投入的时间比重是最大的,其它工作自然会有顺序排列。其实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许多道理用在工作中是同样有效的,无非就是整体与局部关系的把握,如果条理清楚了,具体涉及到版画与油画、传统与当代、保守与前卫、教师与艺术家与行政工作等关系,只要分清主与次、轻与重,各种关系自然就能把握好,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例如性格、家庭背景等等。
对我来说,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它们没有让我太为难,这些事情对于我艺术思考和实践的益处大于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如果艺术家能亲身参与到社会急剧变化和各种复杂性的关系中,那么他会得到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和工作方法,这些体验在外围观望是难以感受到的。中国未来的艺术发展不同于西方艺术的关键所在可能就是源自其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至少在我看来,参与到社会进程当中,有助于深入体验深层次的社会脉动,有助于艺术家的思考和创造。
10)能否谈谈最近的创作计划?不久前红门画廊为你举办的大型装置作品展可否看成是你未来创作的一个新趋向?
我近期的创作计划多是在尝试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制作方法,当然同时也在想一些问题,总体上来说,我现在做的都是一些尝试性的东西。具体来讲,一是对绘画中光和影的语言探讨;二是尝试一些材料语言,最近有一个项目正好为我的尝试提供了机会,就是为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制作一件装置作品。这座博物馆是矶崎新设计的,这个创作项目也是由他策划的,共有十位艺术家参与,除此之外,我还计划做些新版画。总之,我不太愿意固守一种既定模式,当自己有感觉和有想法时就想尝试,不大去想作品是否会被认可或名利上的事情,我只想顺其自然,这样才会让自己真正体会到乐趣,心里也会感觉到踏实。
红门画廊为我在榆舍饭店做的装置作品展,实际上由于空间和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实现这件作品的完整意图,我只是把它当作一次活动来对待的。这件作品原是为纽约的一个空间所做,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无限期延迟了,因为运输、保险、布展需要很多资金,所以只能等经济好转后再实现。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有好的思路,这类作品还会继续做,不过我很难讲出将来的媒介方向是什么,什么媒介适合表达我的想法,我就会选择什么媒介,这方面对我没有任何束缚。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