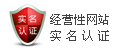日志
日志
蚂蚁的微言大义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庄子•知北游》
蝼蚁是一种微小但无所不在的东西,就像“道”一样,在这里,庄子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解释了“道”的特性。在这段对话中,庄子不仅提到了蚂蚁,也提到了大便,听到大便这个字眼时,东郭子就避而不谈了,可见东郭子有心问道却不愿接受“道”在蝼蚁、稊稗、瓦甓,甚至在屎溺之间的可能,简直就是地道的媚俗者,因为“媚俗就是对大便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米兰•昆德拉)
正是为了讽刺“媚俗”和其它的观念樊篱,庄子借助于蚂蚁这么个卑微的小东西在东郭子们的观念大防中制造着“不和谐因素”,几乎就要引发一场溃决。这正好暗示着一种蚂蚁的力量,一种卑微的、草根的、不经意的但却绝对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体现于庄子的寓言中,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寓言中,蚂蚁才具了力量,庄子对“道”寓言性的言说一直流传了下来,以至于蝼蚁成了一种象征形象,一种关于蚂蚁的力量的微言大义。
陈志光的作品无疑提示了这种蚂蚁的力量。蚂蚁在他那里有时幻化成了各种古人的身份,武士、将军、文人、仕女、乐伎,有时也装扮成当代社会的世相众生。可以说,陈志光给这些拟人的蚂蚁搭建了一个戏台,但他并不是把蚂蚁比喻成人,而是把人比喻成蚂蚁,他向我们呈现的是构成历史的人之本质——人们承受或改变历史所凭借的东西正是那种蚂蚁的力量。
但历史与其说是过去,还不如说是现在,历史的叙述及形象无一不取决于当下人们的认识结构乃至话语规范。在这个意义上,陈志光的雕塑成为了一种文化寓言——关于当代的我们对古代的他们的想像。
“道”在蝼蚁 但“道”不仅在蝼蚁,对于陈志光来说,或许,蚂蚁这个形象仅仅是一种阶段性的选择。
不锈钢:能量的消退
陈志光蚂蚁雕塑的材质是不锈钢,是一种相当现代的材料,也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最常见的视觉因素之一,与不锈钢直接相关的形象是冷冰冰的机器人未来战士。
但陈志光的不锈钢蚂蚁并不显得冷酷,反而显得温情而富有人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对雕塑造型的处理,蚂蚁的不锈钢表面充满生物特征的细节,因此与其说是不锈钢在修辞蚂蚁,还不如说是蚂蚁在修辞不锈钢,不锈钢被灌注了有机生命体的特性。而另一个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不锈钢文化符号能量的消退。工业社会的极境发展早已使不锈钢材料不再停留在一种工业性形象上,技术一旦转变成日常生活,或者说人们在科幻电影中想象出的由不锈钢构成的世界一旦变成现实,作为符号的不锈钢就不再具有符号能量了。因此在这个连家用厨房和卫生间都充满不锈钢物件的现实中,不锈钢的工业野性已慢慢驯服了。甚至与一些更新型的材料相比,不锈钢甚至有了一种相当“古典”的气质。
我不能确定陈志光对不锈钢的使用在主观上是否是中性的,或者说是纯材料学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不锈钢在他的创作思路中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雕塑对于陈志光来说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材质转换的问题。
把一个古典形象的大理石雕塑转换成现代金属或塑料,或者把一个现代的玩意,如电脑、汽车这些东西转换成木质或陶质的雕塑,这实际上是在试图调动材料背后的文化含义,即把材料当作符号,然后再把当代艺术的创作简化为符号的并置或错置。这种廉价的创作思路的唯一优点是便于识读,因此便于掌握,于是得以流行,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沉疴的一种。
材料本体价值的呈现伴随着现代主义的出现而开始,但并未随着现代主义的终结而结束,因为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终结只是在指审美自律性的完成,但是材料的本体价值并不限于审美价值。物质在作品中成为材料,意味着物质对自身的抗争,从自在趋向着自为,从而进入了一种主体与世界的表征关系中。这种表征关系,可以是再现——世界决定主体;也可以是表现——主体规定世界。现代主义怀疑并搁置了这种表征关系,强调材料的自律,即非表征性,但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休克疗法”似的策略,因为材料彻底的自律即意味着材料退回了物质,回到了自在性存在的无明之中。
格林伯格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审美性成了材料的避难所,审美牵扯着人性,允诺了主体的完成。但这种危险掉进了一个更大的危险中,即审美的泛化,审美的形式主义成为了设计,成为了时尚,主体不仅没有在审美中更加明晰,反而被消耗殆尽。这就是我们在当代社会中的经历,也是当代艺术所谓当代性的针对背景,这个背景可以简要的描述为主体与世界之间表征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表征方式,从同一性原则走向差异性原则。
差异性,或者说对异质性的追求使得我们不可能再有一种稳定的符号体系,也不可能再有一种稳定的、自明的叙事。在这个时候,任何的表征都必须涉及到对其前提的自我设定。
落实到材料上,即任何一个艺术都必须给出自己使用该材料的理由,材料不再是艺术表达的基础,因为材料也有其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个体的观念,或者放大为群体的话语。
陈志光使用不锈钢的理由大概是不锈钢的敏感,它的高反射性使得陈志光的蚂蚁可以适合于任何环境,这实际上为其后的雕塑摄影作品埋下了伏笔。同时,不锈钢金属焊接工艺能够恰如其分地呈现出蚂蚁的生理结构特征。但这些理由是否充分?
雕塑摄影:被凝视的伪装
雕塑一旦从空间审美转入文化寓言,它就需要一个背景,或者说设定一个理解的场域。因此,对于陈志光来说,以摄影来框定他自己设定的语境与观者的目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使其雕塑中所含的文化寓言独立构成了一个篇章。
雕塑经过这样的转换就成为了图像,它放弃了三维的空间、直接的体量与实感的肌理,放弃了环顾的观众而诉求着凝视的观者。也正是在观者的凝神关注下,陈志光的蚂蚁仿佛成为了一种意象。
荒野、古道、废城与颓楼,放置在这些地方的不锈钢蚂蚁注定带来一种奇诡的意境。作者似乎想把观者卷入到思古情怀中,但又似乎是在断言着“古代”的不可挽回。换句话说,陈志光所做的是模拟古典美学,并刻意留下了伪造的痕迹,他的雕塑摄影如此,其雕塑本身也是如此。因此,陈志光是在反讽着人们的“古代想像”,或者说我读出了他的反讽:
表面是一本正经的先秦式的古典寓言,这个寓言是建立在一种“古代想像”之上的,但陈志光却抽去了人们“古代想像”的完整性,因此他潜藏着一种现代寓言。现代寓言,或者说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就是宣布概念的不完满性,即断裂。最后,我要用本雅明的话来结束这篇多少有些离题的评论:
“历史”一词以瞬息万变的字体书写在自然的面孔之上。悲苦剧搬上舞台的对自然—历史的寓言式面相在现实中是以废墟的形式出现的。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中。在这种伪装之下,历史呈现的与其说是永久生命进程的形式,毋宁说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的形式。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