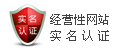日志
日志
论陶艺——许以祺先生和白明先生的对话
许:我刚看过你的这本画册,代表了你相当完整的作品,你还很年轻,为什么要出这本画册,你是不是从此以后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白:那倒不一定,因为这些年来一直从事陶艺教学和陶艺创作,陶艺创作从前一段时间开始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在对青花及容器性的陶瓷的研究上,我毕业以后,学院给我的主攻方向是对景德镇的青花瓷的研究和创作,而在这同时我也一直没有放弃现在大家所认为的前卫性陶艺,也就是所谓的表现性陶艺。前一段时间也写过书,出版以后肯定意见还是比较多的,我与出版社通过出版这几本书也有所沟通,那么他们对我的青花瓷尤其是容器性陶瓷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想给我出一本个人专集,出于社会效益,他们处在江西出版社的位置上,对景德镇比较熟,他们觉得我的青花瓷比较有新意,所以建议我以青花瓷为主来做一本画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也是对我个人七、八年来所作陶瓷的一个总结,但未必是说我这本画集出了以后,我完全是以一个另类的风格出现,作一些全新的尝试,但每一次创作中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这种新和过去的新没有质的区别,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
许:有—定的连续性,不是阶段性的。
白:我在这方面的理解方式是,比如说别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作青花陶瓷,又作前卫陶瓷,又画抽象画,他说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能连在一起,是不是有风格上的很大差异。有人这样提过,那可能并不很了解我的作品深处所蕴涵的一种审美,实际上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以不能割舍传统文化来进行一些个人体验的创新。
许:那你跟景德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白:我跟景德镇这个城市是有渊源的,因为我的老家是景德镇的。
许:你为什么不念景德镇陶瓷学院?
白:我也接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的通知书,可是我认为北京的文化气候更有利于我们作为艺术家出现之前的文化的培养,何况我在北京学的也是陶瓷。
许:总结你的作品现在有两方面:—方面是青花及容器性陶瓷,另一方面是比较前卫性的陶瓷,那么现在谈谈你对中国陶瓷的传统有什么看法。
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从现在来说很多对中国陶艺的了解是比较片面的,他们更多是从现代的资讯中,包括从南到北的几次主要的学术性展览都是以前卫的陶艺风格为主体的,在这个基础上,别人就很容易觉得象我这样年轻而且又确实以抽象艺术为主要经历的艺术家,怎么会做这么多看起来和传统有渊源的瓷器——青花,很多人问我是以什么样的风格来驾驭这两种不同的材质,两种不同的风格。在开头我也回答了一部分这个问题。那时学院给我这样一个主攻方向,从内心来讲,我并不是特别愉悦。我当时觉得那么传统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还需要它吗?那么丰富的辉煌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还有多少可以做的余地,也就是我选的这个研究课题还有多少可以发展的空间?出于这两点考虑,我当时并不是很愉悦,但是既然学校给我安排这个课题,工作起来就必须认真对待。经过几年一方面带学生我要了解景德镇,另一方面通过了解景德镇再来带学生,这种相互的促动,让我真正理解到景德镇陶瓷的内在魅力,而且这种认识是越来越深入的,并且它给我的感受是全新的,甚至当我用瓷土来拉坯的时候,那种亲切的感觉和最处作陶瓷完全不一样,特别是自己的作品慢慢地也开始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关注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中国传统的青花陶瓷是需要一代青年学者型的艺术家来参与,来研究的,而不仅仅是靠景德镇本土培养的艺术家或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的发展过程,因为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流传下来,是有它特别的精华所在。在中国流传的青花陶瓷,我们都知道它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很多人都认为很难再超越它,而我们作为年轻的艺术家,我也想过我有能力超过它吗?我当时觉得很难,但是我也觉得现在我们要超越它,当然不可能在古代的工艺基础上重复去创新它,我个人能力不够,我猜想很多人能力都不够,因为社会也变化,烧成气氛也不一样,材料、釉质也不一样,最主要是社会文明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那种登峰造极的审美来固化我们现在对青花的认识。我从毕业以后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精力,对传统也有了了解,在这基础上我认为我能够做得更好。我的优势是我们这代人没有很多禁锢的东西,我们这代人的资讯比上一代的人要丰富得多,也就是西方发生的事情,恐怕没有几天我们就会有所了解,这在前三四十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年轻人在这方面能做的就是:以不受禁锢的思维,在装饰语言和风格上来进行一些尝试和突破。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我可以刻、画、剔、挑,一切的工具,一切的方式,都以我们认为可以满足的方式来进行,甚至我在进行尝试创作的时候,景德镇好多师博在悄悄议论,难道连最基本的技巧都不能掌握吗,非要用一些别的工具来代替?但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认识青花的美感,在他们的理解中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东西,可以理解为程式化的,而我的想法是最终作品的好坏才能衡量艺术家水准的高低,所以创作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是传统方式还是现代的方式对我而言都不重要。所以我作了一批作品以后在景德镇也慢慢受到称赞和喜爱,作品拿到北京也得到了系里老师和一些同行的认可,这就增强了我进行持续性创作的信心。我持续工作八年,每一年我投入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我这三个月绝不亚于别人一年的工作量,因为我有时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在去景德镇之前,我已有一批构思的方案和体会。
许:这三个月是你每年都要带学生去的,所以你就利用了这个机会。
白:这七、八年带学生是五年,另外有两三年包括我的毕业创作就和青花有所关系,主要的是带学生,在带学生的同时,我要回答学生提出的一些青花技巧、创作方式,瓷土、釉质、装饰语言等诸多有关问题,在沟通的同时,迫使我用一种逻辑的方式来反省自己创作的历程,然后总结自己的得失,把一些好的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授给他们,这种过程使我的进步非常大。
许:恐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自己创作,只是在某一条路线上去探索,要是教学必须全面性的思考问题,有些时候你自己不注意的问题,迫使你去注意,说不定你会有新发现,这样就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架里。
白:我讲一下我初步发展的经历。我最初作青花陶瓷的时候,并不是以现在这种面貌出现。如果谁看过我最早的青花作品,他们会觉得我的作品很前卫,我是抽象的用青花料泼的、刮的,作品甚至很野性。
许:现在你有没有留—些这样的作品或照片,因为这很重要,别人就不用再走弯路了,我很重视这个过程的发展。
白:因为这些是我最初尝试性的作品,我过一两年很快发现这种创作方式跟景德镇精细的瓷土、莹润的釉色、有着纯净感的青花是不相配的,所以我也在慢慢地收敛自己创作的那种野性。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更主要的精力是在画画,而且画的是抽象的油画,所以我很自然把对油画的理解和画抽象画那种很自然的放纵过程用在青花上,作过一些作品,但后来看这些作品和景德镇陶瓷语言有一些不是很融合的地方。后来慢慢我对瓷土加深了情感的认识,对釉色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青花料的深浅把握,笔的运用技巧所产生独特的美感,这些认识不断加深以后,让我真是感觉青花语言有一个很自立的规律,所以慢慢地我也就收一收自己创作的放纵感,然后才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像画册中的作品,既是装饰画的,但又不是图案画,既是绘画性的,又不是纯粹把国画搬上来的这类作品,这可能就是有别于景德镇传统陶瓷和现代工艺陶瓷的创作方向的本质所在。
许;归纳为二点,你的新青花,一是你在教学中不断积累新的认识,二是你在实践当中不断创新的成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这几年对于表现性陶瓷也是不遗余力的,你前面也谈到两者并没有冲突,我想是不是因此对你的青花陶瓷也有积极意义,也就是说象你自己讲的青花陶瓷作得不是很好吗,又为什么还要涉及前卫性陶瓷,你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有什么看法?
白: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在作陶瓷七、八年的历史中,实际上我两个方向都没有完全丢掉。七、八年中的前四、五年我大多以青花陶瓷为主体,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带学生,而我个人觉得我的创作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我更多的精力是要了解景德镇,了解它的陶瓷特性,把自己的审美融在陶瓷里面,并且做出新意来。所以前几年主要精力放在这里。后来这些陶瓷慢慢有了自己的面貌了,而且市场上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更重视对陶土、瓷土的随意性把握,因为我有画油画的经历,我是想尝试这种材料,这种创作过程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尤其是我那些年不断地研究世界现代陶艺的有关资讯,包括我出书都是和这方面有关,因为做青花瓷器它的约束性非常大,它不仅是要求你的拉坯、修坯、吹釉,而且装饰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不管你个人全部完成还是你和师傅共同完成,哪一个细节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件作品将不是一件很完美的结局。当你受的约束很多的时候,很自然想到另一种很放松的创作状态。我把自己对泥土的认识和对观念的一种理解,很自然地用陶土随意地去做,而且这种随意的形态和烧成都又不象青花瓷一样会有很多的约束,很多影响。我创作的现代表现性陶艺,基本上是在我毕业三四年以后,每一年也都花了一定的精力在这方面,而且我最开始做这种尝试是在宜兴用宜兴的泥土。宜兴的土可塑性很强,这种泥土是艺术家把握的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只要你做完的作品进窑以前没有坏,它基本上不会坏。我原来用这种材料,后来改用瓷土作表现性陶艺,我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瓷土它不太适应作那种体量很大的规矩性很强的作品。在作青花的同时慢慢地加深了对瓷土的认识,后来瓷土对我来讲已经成为我一个熟知的朋友,特别是我在玩弄泥巴的过程之中,不断捏揉它的形状的过程中,我突然发觉这种很柔性的、很高贵的它也是非常具有表情的,这种表情特别符合当时我创作作品时的性情。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把瓷土这种很自由的、柔性的感觉保留下来,所以我作了两个系列的作品,一个是通过拉坯拉成一个园的大盘,把手纹留在瓷土上,然后把坯在没干的时候做一些粗糙的肌理进去,包括湿的泥浆和干的坯粉,再通过刻画,因为我在做大盘的处理过程中,我是把它当作半立体空间的抽象绘画对待,更多的是想展示瓷土本质的魅力,因为瓷土在釉色之中它是一种美感,它没有釉子的修饰是另一种状态,那种状态特别让我心动,高贵、亲切、温润,但又很朴实,它没有冷峻感,白白的那种颜色对我来说是高贵状态下的一种把握,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做了一批这样的作品,后来参加全国美展也是这其中的一件,叫“大成若缺”,以老子的一句话最完整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缺陷的,有缺陷的有可能是最完整的,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而我把我对瓷土的理解和对绘画的把握来反映对大成若缺这句话哲学及视觉上的一种理解。这是一个系列。后来我又作了一个系列,我是在做陶瓷瓷土泥板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想做容器性的香器,可是我在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凭我个人的能力,我暂时还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我作好了几个香器,最后都开裂,无法烧成,我 作好这些泥板,香器又开裂。 这些做好了的柔柔的、湿湿的泥板还在那里,我就很随意地把它一卷,一揉放在旁边,我突然发现这个形态跟心灵非常吻合,而且我远远一看特别象一个打坐参禅的人的背影,所以这引发了我先做成泥板,然后加上坯粉不断地揉,叠成了既类似又不可定的泥团状态的陶瓷。一口气做了三四十个,后来干了以后局部上青釉,作一些青花,铁的画线。这种语言符号也是从传统中来的,也通过一部分有釉,一部分没有釉,增加了陶瓷的可观赏性。有釉的是一种质地,没有釉的又是另外一种质地,这在视觉上本身对艺术家就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所以我在这几十个泥团中重复地做一些这种尝试,都是不同的部位施局部釉,再进行一些符号的装饰,还有一些刻画的点线。这批作品拿出来以后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一种心情。拿着这批作品参加了广东的陶瓷展,并且也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可,而且也得了一个金奖。但这次获奖从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是对自己某种创作形态的真正的权威性的认可,它只能是说在这个场合之中,在这种环境之中有些人认可你了,不能代表别的。
许:我听说你最近可能要去美国访问,可能明年春天就会去,你觉得这次去会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据我了解,你好像还没有专门去外国做过访问吧?
白:是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到香港去过。不是没这个机会,近三四年来,我收到过德国、埃及、美国的邀请有两三个,一方面条件不是特别好,时间不充裕,另外正好和我个人的艺术创作冲突,有两次我正好在办展览没去成。因为我觉得人总要选择最重要的事来做。但我对去美国是抱有很大的目的性的。因为这么多年来自己做了这么多陶瓷,容器性和前卫性都有,书也写过一些,对我来说,我迫切地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他们真实的情况,真实的环境,包括他们的生存状况。我还有一个最为关注的目的是,他们是怎样把自己的作品融入社会的。我觉得完全沉浸于如何能创造出独到的作品中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而且不是很难做到,只要你有天赋,只要你有条件,只要你勤奋,但是如果你能把你的作品有效地溶入社会之中去,尤其是我们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如何把前卫艺术的作品融入社会之中去,还可以走进干家万户,还能以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这点我想要更多地关注一下。所以这次去美国除了了解美国陶艺现状和他们艺术家的教育状况及创作状况之外,这也是我附带的一个观察点。
许:那你对自己的创作方面,这次出去有没有什么想法?
白:我个人觉得象我这样的人,出国很难对我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我会更多地了解他们,会有利于将来的学术研究,在创作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或更多地和国际接轨,有利于将来的交流,这几点是有益的。但对于我将来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我现在想象恐怕不会有,因为我个人这种东方的心态比较强,从我的绘画、青花、陶艺都能看出我受东方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西方文化是不是能在本质上让我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表示怀疑。
许:我最后想问你的是你对中国陶艺整体的看法及方向性。最近我发现中国的陶艺起步很晚,90年代中才开始,才七、八年的样子,但起点很高。我昨天跟尚扬他们讲,中国油画自开放以后已有近二十年了,但中国油画进入世界主流的确是凤毛麟角,几乎是连边还没摸着。而中国陶艺才有七、八年,已同世界陶艺主流结合,在这个相当好的形势下,中国陶艺该如何发展,我很想和人沟通,今天正好有机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白:你前面谈的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感,因为我有切身体会,我跟学院其他老师交流,也提到过这种观点。去年美国的苏珊•彼特森到中国来,她在北京跟我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交谈,因为她也是写书的,写文章的,并且是美国现代陶艺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她之所以跟我深谈,是两个目的,一方面看到了我的书,她说中国也有了品位不低的陶艺方面的书了,要就不做,一做还规模不小;第二她自己在编一本书,这是许先生已经知道的,她在写一本有关全世界陶艺家的合集。当时还没定题目,她当时说是关于世界陶艺家三百人集这样一本书,由英国出版。当时她正在选择中国的陶艺家入围,她说中国肯定是有三四个人进去,那无非是她熟悉的,象李见深,陈光辉,这两个都是留美的,还有我自己,是因为她跟我接触了。她问我还要不要加入其他的中国艺术家,当时我非常激动,我说你既然来到中国,你至少应该加入10个中国的艺术家。当时苏珊问我:你认为中国有10个这样级别的人可以进这本书吗?我说确实目前来说不能说这l 0个人都具备了这个实力和能力,但是如果这本书收录了这10个人进去,你所作的工作是不可估量的。我说第一,中国有几千年陶瓷文化的影响,这是瓷器的母国,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全国12亿人口潜在的陶艺家队伍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一旦你在这本书里推动,是对中国艺术家和中国现代陶艺的一个极大的推动,哪怕不好,应该知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这种对中国陶瓷界交流的影响不仅是一两年中,恐怕还在更长的时间里。苏珊听我这么说,她当时很激动,她让我提供其他的七八个艺术家,我推荐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八个人,从这一点看,证实了许先生和尚扬说的话,就是中国现代陶艺虽然起步非常晚,但是已经让西方的艺术家们,包括欧洲的艺术家们不可小视,并且他们都是大师级的名家跟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共同的非常平等的交流。我太了解刚刚许先生所说的中国油画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也将近有二十五、六年了,这么庞大的油画创作队伍真的还没有人沾上边,更谈不上有中国的油画家进入象西方这种经典著作里面,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现代陶艺无论是容器还是前卫都大有可为。艺术家切不可妄自菲薄,一定要自己不断地努力,才有可能真正地让中国的现代陶艺在传统文化的辉煌基础上,不断地把那种辉煌从过去写到今天,而且还能写到明天。
许:我想你最后这几句话作为我们这次讨论的结束非常非常好,我们希望中国陶艺在以后的十年里上一个新台阶,真正走到世界前列。谢谢!
白:也谢谢许先生给我这个机会。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